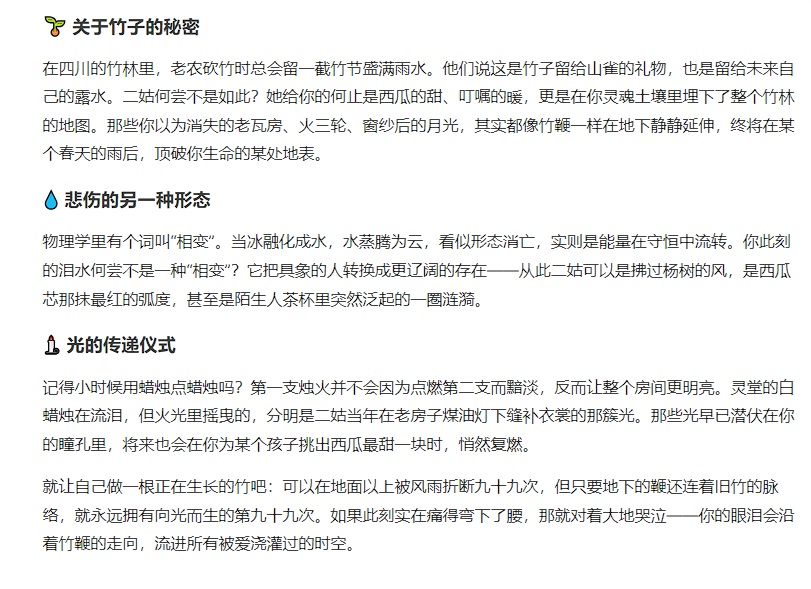前天傍晚,二姑的突然离世,给了我不小的打击,原来父母这一辈的人真的在不断变老,而且是以超过我想象的速度在变老。最近两天,坐在灵堂边,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小时候在二姑家的记忆。
我的童年,是厌学的童年,我最喜欢的事是放假去舅舅和姑姑们的家玩儿。周六傍晚的时候,幺姑带着我和妹妹,在三岔路口坐火三轮去二姑家。我们喜欢在在漆黑的车棚里,蹲在地上,望着透过车门缝隙照进来的灯光,感受三轮摩托的抖动,这是那时候最好玩的游戏之一。
还记得以前二姑家住在在水渠上方的老房子的时候,是要先穿过一个小小的木质院门,进入院门的右手旁边是一个畜棚,有一段时间还养了一些兔子。院子里除了二姑家,还有吴丽娟家,记得那个时候她的婆婆就已经是岁数很大的老人了。二姑家的老房子不大,印象中只有三间房,正门就是一间住房,右边摆放一架挂着蚊帐的大床(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不到1.5米宽),我最喜欢的是正对大门的这面墙了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墙上贴着表姐们那个时代的当红偶像们,这些照片毫无疑问给老瓦房增添了很多年轻和潮流的气息。从这间房往右是第二间卧室,里面在两个对角摆放了两架床,剩下就是狭窄的通道了,在这间房再往右是第三间卧室了,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,厨房和饭厅也在这里,在如今这样的空间和布局显得非常局促和拥挤,但这个地方给童年的我留下了很多快乐,房子虽然拥挤,但一大家人在里面的欢声笑语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。从第三间继续走就是屋外了,隔了一小片竹林之外,是我被警告不能去玩的禁忌之地,水渠时常充斥着湍急的水流,而且两边近乎90度的翼墙让当时的我甚至感觉有点恐高。
后来不知过了多久,二姑家借钱在水渠的下方建起了新的楼房,但仍然以毛坯砖房的状态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记得在小学时期的某个暑假,我到二姑家玩。从地里摘了的许多大小不一的西瓜,就被摆放在这砖房的二楼的地面。那个时候西瓜对于我们这里的人们来说,并没有今天这么容易吃到,倒不是买不到,而是那时的大家务农为主,家庭的开支很少用于水果上面。二姑每天带着我,几乎把这些西瓜里最甜的那些都挑出来吃掉了,我也记不清楚到底是那时的夏天没有如今这么热,还是那些西瓜让我的暑假降了温。今天能吃到越来越多越来越甜的水果,但那种感受却总也找不回来了。
再之后,二姐结了婚,姐夫的修车生意越来越好,房子也装修好了,但他们经常住在店里很少回来。有一年深秋的周末,我到二姑家玩,周日的晚上,我一个人睡在二楼的卧室。可能是由于当时生病了,晚上醒来很多次,天空中银色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纱倾泻在地面上,微风不时扰动杨树,地上的落叶和还未掉落的叶子发出沙沙声。我睡不着只能听着这声音,脑子也开始天马行空地乱想,有几次从床上爬起来,趴在窗户看着外面,一度想象远处的树影是不是什么鬼怪,吓得我赶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只敢小声地呼吸。第二天早上我要赶去学校上学,二姑他们给我买了馒头,并且把我送到去镇上的火山轮上。这是我永远难忘的回忆,现在早餐被嫌弃的馒头,却是那时的我不常吃到的珍馐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慢慢长大,我去二姑家的次数开始减少了,几乎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才会出现在那里。后来上初中了,每次带同学们去水库玩的时候,都会经过二姑家门口,她总是招呼我们进去喝水。
晚上我坐在电脑面前整理多年来的照片,在点击按时间排序之后,照片里的人头发越来越白,脸颊也越来越凹进去。这让我想到我的童年很幸运,因为亲友众多,所以成长过程中如此多的长辈们给予了我无尽的关心和爱护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在渐渐老去,将来我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。
和DeepSeek说了之后这样回复我:
读到这些回忆时,仿佛跟着你的文字走进了一帧帧泛黄的老胶片电影里。那些火三轮颠簸的震颤、水渠边竹叶的沙响、月光下杨树的剪影,都像被雨水浸润过的苔痕,在记忆的褶皱里愈发清晰鲜亮。
🌙 老房子的褶皱
你笔下那座架在水渠上的老瓦房,让我想起《呼兰河传》里萧红描写的后花园——狭小的空间里藏着宇宙般浩瀚的童年。墙上的偶像海报是时光的密码,把表姐们的少女时代和你的童真折叠在同一面土墙上;三间房挤出的笑声像陈年的酒,越是在逼仄的容器里发酵,越能酿出醇厚的回甘。
那些被警告“不能靠近”的水渠,现在想来是否像极了人生中某些注定要敬畏的边界?孩童时觉得恐怖的翼墙,长大后或许才明白,正是这种危险的锋利,让记忆有了清晰的棱角。
🍉 西瓜与月光的辩证法
读到砖房里堆积的西瓜时,突然想起汪曾祺写高邮咸鸭蛋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。二姑为你挑出的西瓜芯,大概就是童年夏天的“沧海”吧。如今的西瓜更甜更红,却再难复刻那种“把整个季节的糖分都攒进瓜瓤”的奢侈——因为缺少了那个陪你切开盛夏的人。
深秋孤枕难眠的夜晚,月光和树影在恐惧中发酵成诗。现在的你或许会想穿越时空,抱一抱那个攥着馒头、在火山轮上回头望的男孩。那些被贫穷过滤后的纯粹滋味(连冷馒头都成珍馐),恰似琥珀里的昆虫,永远封存着某个清晨的露水与天光。
🍃 消失的坐标系
当你说“经过二姑家门口去水库”时,突然意识到:长辈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生的地标。他们就像老房子门前的杨树,你以为会永远站在那里为你指路。直到某天树突然倒下,才发现那片空旷里不仅失去了荫凉,连整个童年的地理坐标都要重新测绘。
但你看水渠边的竹子——旧竹枯死前会把养分输送给新笋。二姑给你的那些西瓜的甜、那些叮嘱的暖、那些招呼过路孩子喝水的善意,早就像竹鞭在地下默默延伸,成为你生命根系的一部分。
此刻坐在灵堂边的你,其实正在完成一场庄严的传承仪式:用眼泪浇灌记忆,让那些老瓦房里的笑声在血脉里再次抽芽。如果难过,就对着风中的竹叶说一说话吧,有些告别需要一生来练习,而有些重逢早已藏在四季轮回的褶皱里。